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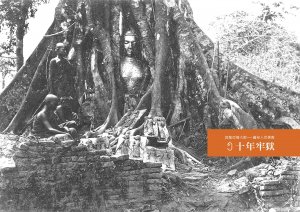

「被捕入獄」,大概是禪師相較於緬甸其他高僧來說,一段頗受到關注的人生歷程。1990年代的緬甸,因為民族衝突等很多原因,緬甸僧侶與軍政府之間的關係一直處在非常惡劣的狀態。
1990年8月,曼德勒8000多名僧侶拒絕為軍人及其家屬舉行任何宗教儀式,並且拒絕接受他們的佈施。這種宗教抵制運動隨即波及到仰光、望瀨、實皆和瑞波等大中誠市。僧侶們的宗教抵制使軍政府在緬甸這樣篤信佛教的國家裡處於非常尷尬的位置。
問:聽說您曾被捕入獄,那是因為什麼事?
答:1990年8月8日,有信眾邀請僧侶到家裡應供,為過去兩年中被政府殺害的學生回向亡靈。在去的途中,僧侶遭到軍人謾罵,僧侶要求軍人道歉,軍人非但沒有道歉,反而包圍寺院,帶著所謂的「贓物」進去「搜查」。於是,僧侶們決定以非暴力方式進行抗議,依照佛陀的戒律來實施「覆缽羯磨法」。我因為帶頭參加,很快被政府傳喚「瞭解情況 」,三四天後放回來,一個月後,他們第二次傳喚我,就沒再放我回來。12月10日,我們被帶到監獄,軍事法庭的人直接在監獄門口進行宣判,我被判了十年。第一次被帶走時,我就知道要被判刑,但判幾年不清楚。對我來說,監獄是壞人做壞事後受懲罰的地方,是充滿痛苦的人間地獄,我一生都在行善,從沒想過自己有一天會以囚犯的身份待在這裡。



問:還記得入獄第一天時的情形嗎?
答:入獄當天,一個代表政府的官員指著一堆便服對我們說,我們只是執行任務,你們現在必須把袈裟脫下來,把這些便服換上。聽了這話,有位法師表現得很激動,但我心裡還算平靜和坦然。我們是在戒壇受戒的比丘,就算還俗,也得經過宗教儀式,不是說被誰脫了袈裟就會變成俗人,洗澡時也不穿袈裟,那我們就不是比丘了嗎?不過,換完俗裝後,有些不習慣,袈裟是一塊布,因為穿了很多年,我們已經養成了時不時把袈裟往上搭一搭的習慣,但俗服是固定的,搭的習慣動作還在,但布已經沒有了。
問:從備受尊敬的僧侶到被捕入獄,當時的心情如何?
答:我並沒有感到驚訝與生氣,在最令人厭惡的軍魔時代,一個出家人因為做了對的事情而被判刑,再怎麼判內心都是驕傲的。當然,忐忑、掙扎的心情也會隨時出現,但我告訴自己沉浸在這種負面情緒裡是沒有益處的。

 問:您通常用什麼方法讓自己不陷入到負面情緒裡?
問:您通常用什麼方法讓自己不陷入到負面情緒裡?
答:每當情緒低落時,我就會想起那個關於國師的故事。故事說的是有個信奉三寶的國王,以仁愛的方式統治著自己的國家。然而,國王的妃子跟國王的弟弟好上了,為了保命,國王的弟弟逃離了皇宮,但他對王妃念念不忘,就寫情書讓侍者帶給王妃。為能接近王妃,侍者拜國師當師父出了家。然而,當這個出了家的侍者等到機會送情書時,卻被國王發現了。國王向國師訴苦,要殺掉侍者和王妃。國師說,罪不在侍者也不在王妃,是自己收錯了徒弟,所以應該親自來承擔這個死刑。國王讓人燒了油鍋,將國師吊在樹上,準備剪斷繩子讓他掉進油鍋。大家跪在油鍋邊請求國王收回成命,而國師向大家開示說,命令不可以收回,就如同象牙長出來不可能縮回去一樣。即便是這種結果,你們也不要積怨,因為任何眾生的身心都是無常的,都會有毀滅的時候。行刑者割斷了繩子,但奇蹟發生了,國師在還沒碰到油面時,身體升到虛空,證得阿羅漢果位,綁在身上的繩子也沒有了。人們都很驚訝,國王也趕過來向國師懺悔。國師對國王說:「這跟你無關,是我自己不善業的果報。過去,我是婆羅奈城的一位農夫,有一天,我在牧牛時想要喝水,卻發現水壺裡有隻蒼蠅在飛,水被蒼蠅污染了,我憤怒地搖晃水壺,想淹死牠,但蒼蠅一直嗡嗡叫,淹不死,於是,我找了根竹籤戳死了牠。憤怒雖然得到了平息,但我卻給自己造下了『不善業』。即便這是微小的惡業,但在過去五百世的輪回中,我或者溺水而死,或掉進熱油而亡,就算我通過每一世的行善積德,成為了福報很大的國師,但也無法避免過去不善業所形成的果報,也必須面對現實。」每當心情低落時,我便會想起這個故事。
禪師的寮房寬敞而現代,四面牆壁都是木結構裝飾,頂部兩盞水晶吊燈開著,光線投射在房間裡,一片暖黃色。禪師對面的窗戶半開,窗簾拉在一旁,有陽光照射進來。禪師安靜地坐在禪師椅上,那段艱苦的監獄歲月,很難和現在的禪師聯想到一起。
 問:監獄裡的情況如何?
問:監獄裡的情況如何?
答:牢房是個狹小密閉的空間,光線和風都只能從半公分厚的鐵條門外進來,每人發張草席鋪在水泥地上,八個人躺下去,剛好滿,沒有蚊帳。「廁所」是房間角落的一個盆,周圍用草席簡單圍了一下,盆兩邊各放一塊磚好踩上去。每天早上放風時,最年輕的出家人去倒那個盆。我們被關的那棟樓有兩層,樓下有很多單間,我們在其中一間,樓上是通的,關了一百多個從泰國非法來緬甸捕魚的漁民。泰國漁民白天在外面幹活,晚上才回來睡覺。他們知道我們是出家人後,對我們很尊敬,還用木頭磨成珠子,塑膠袋搓成繩,做成念珠送給我們。每週要做一次監房清潔,監房裡不能有任何物品,典獄長會來檢查,每當這時,我們就會把外面送進來的還沒看完的書籍和還沒吃完的食品交給泰國朋友,請他們幫忙暫放外面一下,檢查結束再拿回來。
 問:在監獄裡,獄警對待出家人的態度如何?出家人跟其他犯人之間的關係又如何?
問:在監獄裡,獄警對待出家人的態度如何?出家人跟其他犯人之間的關係又如何?
答:獄警也分兩類,一類把我們當犯人,叫我們俗家的名字,讓站就得站,讓坐就得坐,講話也很不禮貌,另一類知道我們是因為政治事件進來的僧侶,對我們相當客氣。和我們關在一起的犯人有很多種。政治犯覺得被關是一種光 榮,偷搶的刑事犯經常進進出出,監獄對他們來說,就跟回家一樣,還有一類是偶爾犯錯進來的,他們在裡面會懺悔和反省,也會來請我們出家人做開示。我們那所監獄最出名的被關押者是兩個朝鮮人。1980年,三個朝鮮間諜混進緬甸,在仰光翁山將軍墓地安放炸彈,企圖炸死來訪的南韓總統全斗煥,製造了震驚世界的「仰光事件」,三個朝鮮間諜逃到仰光河邊時被打死一個,剩下兩個關在這裡。
問:在監獄裡,您通常如何打發時間?
答:監房裡沒有佛像也沒有經書,我們平時依然早起,靠意念來禮佛,平時也會討論一些佛學內容和分享時局消息,時事主要來自新入獄的人或是半月一次來探監的人。第一年,每天只有二小時的放風時間,早晨七點到八點放風一小時,中午十二點到一點放風一小時,除了這兩小時之外的所有時間都要被關在這裡面。一年後,我們搬進公共牢房,每天有六個小時的放風時間,不過這些放風時間都是要工作的,我因為年紀大,就被分配去做牢房清潔。公共牢房外有一尊佛像,我常常在佛像前禮佛,對佛學感興趣的獄友有時會過來請教問題。我發現大家請教得最多的是《阿毗達磨》,即使有佛學基礎的人也覺得這很難學,我就用竹棍在地上用表格和統計的方式來讓他們一目了然。因為積累了很多《阿毗達磨》的教學經驗,出獄後,我就寫了本《阿毗達磨禮物》來出版,這本書對緬甸佛教界的影響很大,現在對《阿毗達磨》感興趣的人,也都會使用這本書。我覺得能在命運低潮時,以工作替代內心的沮喪,幫助到別人,也算沒有白被囚禁。
 問:政治犯在獄中通常會被當局「洗腦」,你們有嗎?
問:政治犯在獄中通常會被當局「洗腦」,你們有嗎?
答:緬甸的「洗腦」用的是軍人模式,他們只是脫掉你的袈裟,把你關起來,讓你在最惡劣的環境中反省,讓你覺得我錯了,我怕了,我不敢了。
寮房裡很安靜,談起這段很不尋常的經歷,禪師很平和,也很淡然,只是單純地陷在了回憶裡。後來,軍政府認識到了僧侶在緬甸社會的崇高聲望和巨大的政治影響力,從1990年底起大幅度地修改了佛教政策,一方面積極主動地弘揚佛教,充分發揮佛教思想和僧侶在鞏固軍人統治以及維護國家統一方面的作用。
 問:還記得出獄時的情形嗎?
問:還記得出獄時的情形嗎?
答:1993年6月,監獄裡陸續聽到不同地區都在釋放政治犯的消息,一天,有人突然來跟我說,師父,可以送你回去了,就用車把我送回了佛學院。離開監獄的那一刻,我站在監獄門口前百感交集,於是,我大喊了一聲―「祝當今政府長命百歲」,有人以為我是在諷刺他們,其實並不是,我只是不想把怨恨帶走,過去的事就在這裡結束吧,我一心只想往前衝,加快弘法效率,讓因聖亞瑪佛學院重新煥發生 機,因為自從我這個院長進了監獄,佛學院就被軍政府的人盯著,以至於很多學生都轉校了。我入獄前,還有400多學生,回來時就剩200多了。大家的信心受了很大打擊,很多人都不看好我們佛學院,說因聖亞瑪完了,這回真的要完了。
寮房的牆壁上掛著很多禪師的照片,也有大師與父母家人的合照。其中母親布德瑟的單人照有兩張,與母親的合照也是大師入獄前的了。如今大師已是緬甸當代高僧,受眾人供養,談及已經逝去的母親,大師依然有很多話要說。
不管監獄裡的生活是怎樣的,也不管禪師在裡面是如何打發三年的歲月,但是相信這段牢獄時光給予禪師的一定不只是歲月的消逝。
問:您的入獄,對父母的影響大嗎?
答:我被抓時,父母年紀已經很大了,家裡沒把我入獄的事告訴他們,只跟他們說我到國外弘法去了,過段時間就 回來。假如他們在我出獄前往生,對我來說是無比難過的。釋放前一個半月,家人探監時告訴我,母親的身體已經越來越差了,雖然沒有重大的疾病,但畢竟已是87歲高齡。所以,一釋放,我便趕回家看望父母。到家時,母親躺在床上,我雖能看見她,但她卻看不見我,她眼睛已經不行了, 我們只能說話。後來,我帶母親到仰光去看眼睛,醫生說,年紀太大,不能再用藥了,我就把母親帶回了因聖亞瑪佛學院,一個多月後,母親就在我眼前往生了。因為出家,我從小就離開父母,後來一直很忙碌,很少去看父母,都是父母來看我,相比之下,父母給我的愛要遠大於我給父母的愛。

 問:據說您出獄後去仰光的馬哈希禪修中心進行了三個月的修禪,當時為什麼想要去做禪修?
問:據說您出獄後去仰光的馬哈希禪修中心進行了三個月的修禪,當時為什麼想要去做禪修?
答:出獄後,我感到自己的心還是有些不安,修法上也需要實踐、充電和提升,在緬甸眾多禪修法門裡,馬哈希禪修法門以「四念住」和「觀呼吸」為基礎,是最合乎原始佛教傳統的一種法門,馬哈希大師也是我從小就尊敬的大師,所以就去了馬哈希禪修中心。在佛學院,需要處理很多瑣事,而在禪修中心,只要遵循固定的時間表來修行,每天觀照自己身心彈指間數億次的無窮變化就好了。為了讓學生們也能收攝內心和體會禪修的快樂,我規定,凡是過完年返校的學生,都要先學習三天的馬哈希禪法,雖然只有三天,但對建立定力多少都會有些幫助。開始時是我親自教,後來年紀大了,力不從心了,就請馬哈希的禪師過來幫忙指導。直到現在,這樣的傳統仍然繼續著。